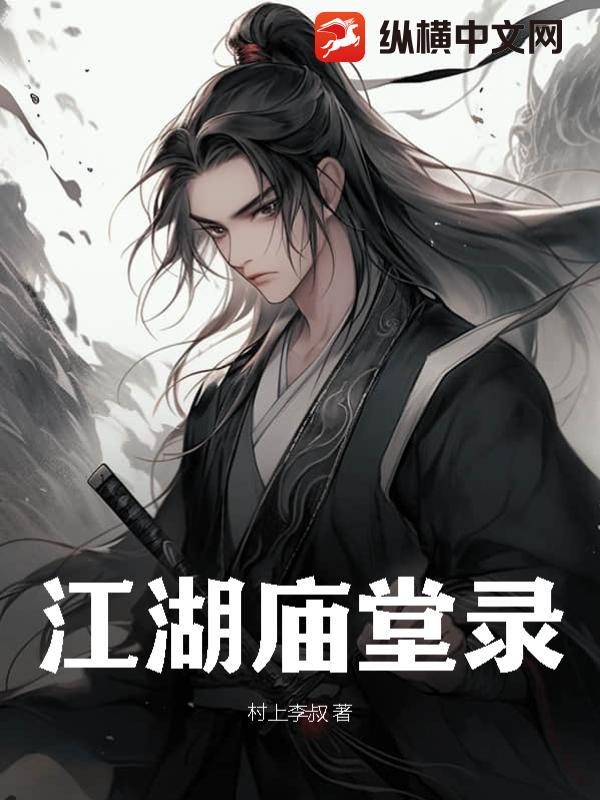李亘坐下来慢慢和田不乐商量,既然已经找到了上官招财等人敛财的罪证,就看如何入手处理,一直等下去不是办法。
“与其苦等,不如放手一搏,多耽搁一刻,他们就多压榨北卫男儿一点血汗,没有战死在沙场,也没有累死在北卫地界上,却唯独死在勾心斗角的自己人手里,这才是最大的不值,要是长此以往,倒不如明哲保身,早些卸甲归田,柔然胡人打过来,死也就死了,倒也比现在爽快。哪像此刻这个样子,为自己打仗,为整个北卫保护安宁,却还要受他人裹挟,我有朝一日要是有机会一定要问问大将军,到底这北卫是他管事,还是这些人模狗样的朝廷败类管事?”田不乐倒不像前几日那样,单凭一身悍勇,浑然天不怕地不怕,守得一身剐,敢叫皇帝拉下马。
殊不知李亘好言相劝,想为了整个北卫考虑,“田大哥别泄气,咱们还是从长计议一番,千万别暴虎冯河,不然北卫就真的陷入困境,难道我们就甘愿认命,任由外敌内患一点点蚕食掉吗?何况这么多忠心不二的真男儿在为北卫付出多少血汗和性命,才换来今日的一点安宁,不如……”
“我也想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不能真连累李兄弟为我们这里的事得罪了真正的权贵,反而失去了沙场效命的机会,这才是北卫一大不可弥补的错失,既然秣马关的事,自然由我们自己处理,大不了拼了,谁也别想好过,最后大将军会亲自出面,我就不信朝廷还真敢对自己人用兵?”田不乐实在是太累了,不只是今日搬运粮银所致,而是多年来积压怨气不得发泄,这才是作为一个血性男儿最大的病态。
李亘很想尽份力,却不知权贵面前,他也无计可施,总不能当着上官招财等人的面,公然指着他的鼻子骂,将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都抖搂在众多将士和骑师面前,或许有小部分跟自己一样身份的士卒会有怨气,却还有大部分的人见风就倒的态势,倒不是这些人跟绝大部分人一样附炎趋势,而是他们惜命,谁愿意与权势作对为敌?那就是跟朝廷过意不去,最后落得悲苦凄惨下场,整个北卫真反了,也等不到今日,李善都没有公然反抗,还不是维持现状,赖以存活着的态势?
何况李善都未说半句话,他们也只是凭空猜测,身处低层,根本就触摸不到高官厚禄背后的衣角,人多不一定就占理。
道理,道理,能说会道,不因人少而崩坏,不因人多就变质,甚至不会被世道左右,被无情风吹雨打过。
可惜与权势为敌就不是什么道理,占不占理也要分时候。
“田大哥要不这样吧?按你的法子办,连夜带着几名信得过的弟兄前去追缉转运使陆大人,只要……”
“兄弟你别开玩笑了,对方可是转运使,且不说有没有走远,就算我们一个营前去恐怕也要吃大亏,秣马关内的军政实权全掌握在上官招财一人手里,我手底下的全是一些从未上过沙场,没有一日提过刀的骑师,马夫,论驾驭逃跑恐怕关内无人能及,但真要打起来,就完全不是个!我刚才也是一时气话,真要弟兄们跟着去涉险,那才是不自量力!”田不乐苦笑凄然,他也不再固执己见,而是看开了,原本双方实力悬殊,朝廷上下又明摆着给北卫使绊子,怎会听信一关之内一群乌合之众构陷之词?
田不乐还是乖乖地回去养马,至于饿不死,就安分地位北卫做事,总不能怠慢了这些年北卫待他有救命般恩情。
他嗒然若失地退出李亘所在的房内。
李亘想挽留,好不容易猜到点证据,没想到北卫真正当家做主之人竟然心灰意冷,这让他“局外人”感到很怅惘失意。
“这事不能让他们得偿所愿,田大哥真要听天由命,就此放任了吗?”
田不乐没有转身,撇嘴一笑,无可奈何地道:“上官狗贼胆敢背着我们将皇粮倒进自己口袋,自然也就有能耐将所有的罪状都掩盖过去,他给你看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东西,更何况朝廷上下一心要置北卫于死地,李兄弟尽早看清形势,还是跟过江之鲫一样随波逐流为好!”
这一点不像田不乐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他这么刚正不阿之人也临阵倒戈了?但又能直接问,这事是他找上自己的,此刻他当面撤回,足显得很仗义了,何况在其任谋其事,既然李亘是前线杀敌将尉,自然是以边关安宁为重,假如在此地驻足停留,边关上的军阵从而延误,那就不是连累而是拉他下水了。
李亘身份一事,还未在饮马川内传遍开来,恐怕也是对北卫最好的保护,若是上官招财之流得知了真实身份,还会这般好生款待?还会这样目中无人?还会这样明目张胆地中饱私囊?
这些都未知,兴许对北卫来说,鲜有人知才是上策,这样便于李亘在北卫地界上彻底看清目前局势,又不损害到北卫真正的利益。
弊端就是他们根本就不会拿一个边关上靠拼命的下等校尉当回事,只会是更加疯狂地自行其是。
田不乐走了,回到他的马场安顿休息,以前的事权当没有发生一样,睡醒了就继续喂马,当马夫,身为军卒只要能有一顿饱饭远比北卫地界上的老百姓要强吧?真是吃饱了饭后就开始东想西想,竟敢和朝廷权贵们作对?
李亘也没有办法,这事不能这样不了了之,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才行,单凭自己和孤掌难鸣的北卫边关上沙场军卒是难以抗衡的,看来只有向李善求以援助,他不是要弥补当年的过错吗?
与其弥补自己,不如真真正正地弥补给北卫。
李亘想好了之后,决定不辞而别,虽然这次灰溜溜地逃走,不是自己不敢豁出命来和他们斗上一斗,更非没有真凭实据,甚至不是实力不济,不足以与他们这群官宦巨寮抗衡。
实在是为了整个北卫着想,更不愿连累那些流血流汗的军卒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既然在李善的管辖地界内,自然由他这位大将军出面,他若是也无能为力,那北卫将彻底完蛋了,更何况出于对自己的亏欠,他不能不管才对,否则北卫不单是他堂堂北卫大将军一个人的,还是百万户北卫百姓的。
——
李亘从饮马川的秣马关独自仓惶逃离,直奔平城将军府,他跟上官招财明争暗斗几个回合都落败了,算是碰了面结下了梁子,也算是无意冒犯,至于责任全由自己一人承担。
出此下策才走这一步,否则怎会向那个恶贯满盈、杀人无数的李善求助?虽说坎水寨他作为大将军亲自解了当时困围,不过眼下的事也非儿戏,上官招财、钱步沟以及朝廷对北卫的局限愈发明目张胆,恐怕就会危及整个北卫,到时候北卫夹在柔然大军和大未权势威逼之间又将祸及多少无辜百姓?
至于田不乐与上官招财等流间的恩怨是否能够暂时隐忍,他不敢去猜想,倒希望田不乐能够听天由命,直待自己请到李善主持大局,到时候他所有的顾忌都会成为顺畅,坤字营一把火烧了军营,给杜亢等人警醒是否有用,他也不清楚?
北卫沙场上拼杀的军卒与大卫朝廷权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厉害,再不加以防备,可不是死几千人,几万人那么容易,到时候却连整个北卫都会被波及,成为炼狱。
北卫担负着防守大卫乃至整个中原大地的门户大任,一旦失守,柔然铁骑大军如同决堤的洪峰一般汹涌而至,淹没蔓延至整个北卫境地,打乱了李善以及他这么多年来精心布局,甚至葬送了数十万儿郎性命换来的今日,更会波及整个大未,乃至中原,甚至江南地界,五胡乱华的历史又将重演……
说什么天下共主,到时候柔然百万大军肆虐南侵,所到之处便是寸草不生,尸骨成山,大好河山被无情蹂躏,到时候天下就是番邦外族横行,华夏子孙再次遭受奴役,宛如地狱。
李亘不想受万世子孙们唾弃,遗臭万年,自己一直痛恨李善是缩头乌龟,没想到一味地忍让换取来不堪想象的结果,还不如恶魔李善呢。
他是一个心里藏不住事之人,但又碍于能力有限,本事不济,甚至无法一展宏图,但大是大非上由不得再躲避,再糊涂认不清,安宁一事决不能丝毫懈怠,北卫的事必须第一时间解决,否则自己门前雪未扫,怎敢心怀天下苍生?
平城位于整个平洲南部,靠近幽州、燕云、太原,统御着整个北卫。
大将军府,李亘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在哪里,也比任何人都要熟悉,自己当年就是从哪里出来的。
当初发誓再也不回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可惜,发过的誓往往总是不得已反悔。
对于别人而言兴许在大将军当差是件风光无限的存在,哪怕就是担任将军府内一名杂役、奴仆、婢女都会向身边的乡亲四邻吹嘘上一辈子,那可是敬若神明般的地方,是整个北卫地界上百姓的信奉,可比拜什么佛祖菩萨要管用,也比见天王老子要体贴实际,为啥?
能以三十余万铁甲男儿,独自据守整个西北门户,让天下百姓免受胡虏铁蹄肆虐,刀刃残害,过上几天相对安稳日子,就这点可就比任何神明要灵验,比天子皇帝的恩怨要实际,这些都是他李善几十年来的功劳,百姓们需要的就是一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他们宁愿相信眼睛看到的实在日子,而不是整日皇恩浩荡的歌功颂德,那些都不足以填饱肚子。
李亘之所以和大家截然不同,他……他是自己负气出走,既不是被驱赶出门,也非外派委任到下属那个州县担任什么官职,孑然一身,灰溜溜地跑出将军府,似乎跟今日很像。
他不够聪明,甚至还有点小心眼,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说的,做事大部分没有什么长性,倒不是他不想去做,而是做着做着才发现,根本没那么简单,想得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还艰险无比,在这个乱世,稍有不慎小命就没了,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或许见了太多的生死后,越发胆小了。
或许长途跋涉,一路上马不停蹄,终于见到了平城的远貌。
纵贯平城就像一座延绵不绝的巨大山峦,蛰伏在空旷辽阔、地势平缓的地界上,又像一头蛰伏深睡的猛虎雄狮,即使原地不动也能感受到它所散发出凌人的气势。
南北纵深两百里,东西横贯三百,在整个大未,除了京都洛阳城能有如此气势恢宏的盛况外,就当属北卫的平城。
北地虽苦寒,地势平坦,当年又是大未开国都城,后迁都南下洛阳,平城也就成了整个大未规模第二的城池。
为了抵御柔然大军,必筑巨城加以震慑,不单是为了驻扎更多的兵马,还能统御整个北卫地界内其他州郡城池,收纳住下更多的百姓。
远处看平城,高耸入云般的城墙,瓮城,城楼,旌旗招展,迎风猎猎呼啸,宛如向世人展示着它的不可侵犯,就是北方强盛胡骑闻风而至,也足可凭借雄风气势将其慑服住。
城墙高达三十丈,足足有三十层楼那么高,远在十里之外就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雄壮,像是天地间屹立不倒的一位巨人,挺拔傲然于那里,任由风雨飘摇,任由战燹铁蹄践踏,它依旧岿然不动。